在母亲好意的安排下,一个从小听话、学习优异的女孩躺上手术台,这对母女并没意识到等待在前方的风险多大。
一场不大不小事故的发生固然有客观因素左右,主人公从小形成的性格弱点同样推波助澜,中注定悲剧的发生,也更值得反思。


第一次提,说的是她一个朋友的女儿:「我今天上街看到了阿姨家那个女儿,你记得吧?漂亮得很呢!但我听说她去做了微整形。确实不怎么看得出来,效果还是可以。」
后来的电话里,母亲又好几次提到整容,从同学说到女明星,最终的结论总是:整一下,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一直以为,这不过是热衷美容产品的母亲喜欢的扯闲事聊,直到有一天,母亲在聊着别人整形的时候,突然流畅地将话题跳转到了我的身上:
整形对我来说,是个遥远而新鲜的词汇。在我成长过程中,外貌没有让我享受过漂亮女孩的待遇,但也从不构成过分的困扰。
又过了一个星期,母亲在电话里说,她预约了一家机构,等我放假马上就可以去咨询一下。对母亲的,我感到可笑又可气:「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,我不想去!」
有些东西,我很早就意识到并接受着:从小到大,在大家眼里,我「可爱」、「聪明」,但换座位时,没人帮我搬过书架和一摞摞卷子,男孩子跟我讨论数学题,就真的只是讨论数学题。对于这些事情,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,没有失落,也没有嫉妒。我勤奋地学习,平和地生活,在喜爱的事情中,获得独特的欢愉。
我考上心仪的大学,继续形单影只地生活,一个人泡在图书馆,一个人跑去看热门的电影,一个人把行李从一层提到六层,一个人接收只可能来自父母的晚安。
舍友已经换了三个男朋友,对象从大哥哥到低年级的弟弟,从乖乖仔到地下朋克。有一次,寝室夜聊前男友的话题,我插不上嘴,悄悄塞上,我在心里问自己:「总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,会觉得吃力吗,会感到难过吗?当然会。」
原来是这样吗?落单是因为我的脸?没有恋爱,不是因为我不想,只是我从未被挑选。我想起那些夸我越来越漂亮的阿姨,更清楚地看到了,她们话语里的礼貌成分。
让一个女孩承认自己不漂亮,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可能需要一刀刀割掉那些自尊心的触角,掩埋那些本能的难过,将压低、缩小,放进那个叫做「普通女孩」的玻璃盒子里。
这个提醒,给我带来的是一种「哲学」层面的困惑:我不明白,为什么这种与「我」无关、我无力改变、且不能选择的东西,会成为我该不该得到某些东西的决定因素,成为我被或者被遗弃的理由。它像一根无法磨钝的刺,反复探出头来,扎在我的身上。但这不是一个致命的困扰,我没有想过改变,只是一次次地,用失落的灰土将它掩埋。
在电话里聊起整形没过多久,母亲体检,查出身体里有一个黑块。医生说,还不能确认是否是恶性肿瘤。
母亲是个细心、周到的人,总是将家里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,即便是长辈们,也总愿意和她商量事情。从小,我就被她精心,整晚陪我解数学题,给我扎繁复的麻花辫,从雨里冲来为我送伞,用她的身子给我遮挡炽烈的阳光。细心的母亲,肯定也早发现了,她的女儿从来不是一朵耀眼的花,别的父母为儿女早恋担忧时,她从未跟我说过什么提醒的话,她知道,没有必要,电话里,母亲一直在叹气。我知道,她害怕了。
「我已经预约好了。你和我去看一下吧。妈妈希望你好。」母亲的意思是,锦上添花,何乐不为。因为这件事,她想让我变美的心情更急切了。
面对母亲不断升级的规劝和唠叨,我曾想了一句对抗母亲的话,我以为,它将具有无以伦比的杀伤力,我大声地喊着:「你们就这么嫌弃我的长相吗?难道不做这个手术我就活不下去?」
说出这句话时,我非常不争气地,带着满心的苦涩和委屈,红了眼睛。我仍然怀有一丝希望,曾试图向父亲求助,希望得到他的支持,告诉我,「没关系,你很好,你没有错,是那些人错了」。
我忽然意识到,我们的对话被封闭在两个真空里,像电影「」中科学家和外星人的对话,双方并不处在有可能彼此理解的语境。
我已经懒得去区分,这个「好」字,是我被情感之后举的白旗,还是我真的为了漂亮,为了活得容易,心甘情愿主动来到了对方的阵营。
今年二月放假,母亲如愿带我去预约好的整容机构咨询,那家机构就位于城市中心区人潮汹涌的购物中心。电梯直达十八层,对着电梯门的巨型粉色招牌上,穿米色丝绸礼服、线条凹凸的女模特五官精致--我未曾想到,未来的七个月,我将无数次在电梯门的开合之间,凝视这块招牌,在这位女模特笑容得体的目光中,自己的混乱与溃败。
我们靠窗坐着,粉色的沙发上,是碎花的图案,明净玻璃窗外景致宜人,玫瑰茶依然温热。我输入挂在墙上的Wi-Fi密码,看一条朋友圈--刚刚在电梯里,图片加载失败。
一位穿白大褂、自称徐经理的女士坐下来,三十出头,淡妆,黑色皮靴。她开始介绍,隆鼻有三种选择:硅胶、膨体和软骨组织。价格依次递增,效果当然越贵越好。软骨组织要从自己身体中取,两处开口,但效果最好,价格也高,十余万。膨体的效果也很好,而且只在一个地方动刀。
徐经理拿着两个透明盒子回来了,以为是母亲想做整形,继续对着母亲介绍。母亲又拍了一下我,我只好关掉手机凑上前去。徐经理立刻明白了,说:
「姐姐,这个你别担心呢,你看看我的!」徐经理忽然把脸凑近我们,「我的鼻子刚做完膨体的,你摸摸,你看得出来的?」
「是呢。我们的医师会根据你们的要求来设计鼻型的,如果你非要做网红鼻我们医师都会的,他们都会为你们定制和调整,肯定不会夸张,就是在你们现在的水准上拔高一点,说白了就是变漂亮了但又说不出来哪里变了的效果,我们机构主打这样的。」
医师的会客室不大,房间依然刷成粉红色,沙发茶几是成套的欧式碎花,门边的墙上挂一面干净的镜子,房间窗户与镜子相对,背后仍然是这座城市的俯瞰景致。马医师进门的第一句就是:「来啦,刚结束一台手术,最近还是忙。」
他高个,笑容温和,大褂的扣子开着,像穿了件白色风衣,看起来不打算坐下,一副只是顺道进来看一眼的样子。
「没事,那你们慢慢聊。」马医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「正好今天下午预约的客人来不了,空出一台手术,我以为你们要约。今天不做的话,未来两周都排满了,过年后再来吧。」
马医师走后,母亲开始跟徐经理讨价还价,徐经理说膨胀体的价格是一万五,母亲想谈到一万二。谈话间,又进来一位高大的中年女人,齐肩卷发,穿一件米色绒毛大衣内搭V领黄毛衣,胸前一块巴掌大玉佩晃来晃去。徐经理客气地叫她「李姐」,她点点头,先让「小徐」经理去接客户电话,然后自己坐下来,继续跟母亲聊价位。
「一万二是有点低了。这样,等会我们空一台,你们这个小手术,准备也不麻烦,今天做了我们这边也不浪费,就给你们这个价吧。早做早好。」
「咨询什么?还有什么不懂的?这个手术我们一个月十几台,半小时的事儿,今天不做等几个星期后也是一样做的--你们再商量下,之后再约也行,但就只能按原价。」
「怕痛啊?傻姑娘。为了漂亮,这点小痛才不算痛。来,我们签个合同,让马医师仔细给你看一下。换个鞋,到手术室里吧。」李姐不由分说。
手术室内开着一点暖风,我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输着液,旁边不锈钢盘子上,玻璃瓶、针管、棉签摆放整齐,角落里放着一台庞大的器械,一个白色的置物柜上也摆满了东西。
这里房间布置风格,和外面差距很大,物品棱角分明,颜色简单有序,两个地方之间,唯一的联结,是圆凳上的小熊玩偶。我居然如此地躺在手术室里,为这突如其来的场景,感到有些。
刚才的马医师走进来,依然是温和地笑着的,跟进来的还有三个。马医师拿起一只黑色马克笔,轻轻在我的鼻子上画了几道。
我的脸被罩了一层医用防护布,他们讲的每一个字我都能听懂,但却觉得,这些声音仿佛漂浮在遥远的地方,与我无关。陌生和不安,同时也在我的大脑中拉起了一层厚厚的隔离布,让我无法思考,也无解目前的境况,一种奇怪的迟钝感,控制了我。
缝合的过程却比我想的还要难熬,或许是药力的衰退,每一针刺入,都有一种圆钝的痛感,我感到自己的身体,像是被心脏起搏器提起又放下的病人,因为疼痛而震动、抽筋、收缩、颤抖。每疼一下,我就数一下,大概八次。
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的时候,医师给我拿了面镜子,我只看一眼就拿开了:我的脸上到处是汗水、皮肤渗出的油、眼泪和血水的混合物。我还在消化刚才的痛感,真的没有余力再去消化这张狼狈的脸。
从手术室走出来,鼻子还在不停流出血水,我把棉签放在人中处,等着它们流下来,丝毫不敢把它伸到靠近伤口的地方。鼻孔里露出好几条黑色的细线,眼睛周围开始显出紫色的淤血。医师在交代护理方法,我什么都没有听。
一个健康的人为什么要主动把自己送进手术室承受痛苦?这是那天在手术室里,一直敲击着我大脑的一个问题。
除了我的嘴巴再也做不出「抿嘴」的动作之外,似乎没有太多坏影响。鼻梁挺拔起来了,两个鼻孔像是修整过后形状好看的山洞。
「不要!」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羞耻,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「羞耻」感来自哪里,但我就是不想在手机或者微信里,存上任何一个与他们有关的联系人。
当我用完第四瓶酒精、第十包棉签的时候,鼻子里的血迹已经开始变白,伤口处出现了肿块,分泌出粘液。我只能停用了所有的洗面奶,但每一次洗澡之后,鼻子里还是会有暗红的血水流出来。
我不得不开始每天去找马医师做清理。我被安排在同一个手术室,酒精、碘、麻药针、清洗针,每天准时操作。
切除肉芽,缝合、护理、消炎、拆线。又一个星期,伤口重新开始流出粘液和血,血停了,又长出肉球。这个痛苦的过程,似乎已进入某种的循环。
一天早晨洗漱时,我在镜子里看到,一道暗红色的血迹横亘在脸颊上,像一把刀将这张本不太完美的脸二次撕裂:睡觉时流出的脓血凝固了。我立即用毛巾擦去,真的好希望是自己没有睡醒、看错了。也许薄薄的鼻孔皮肤上已经扎了数量不少的针孔,但没关系,他们愈合很快,医生说过,皮肤有记忆力。
马医师在每次的复诊观察中,不断给出结论不同的推测诊断。这个机构仿佛有一个无法看到的,一旦靠近它,就会想要它,认同它,并失去所有抵抗力,吸走我身上的和勇气。
为了一个好看的鼻梁,我了七个月,试过所有可能的治疗,在鼻子被针扎成筛子之前,我决定把这个不安分的异物取出。
马医师很早就提出这个方案,我和母亲在犹豫,直到反复的发炎、脓水和酒精气味,将我对鼻梁的留恋殆尽。我克服在花季年龄毁容的恐惧,做好了休学的心理准备,终于拿起电话,和马医师预约了假体取出手术。
手术的前一晚母亲哭了,术后,她才敢告诉我,那晚她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,得知取出手术失败风险极大。
手术依然在那个我已经完全熟悉的手术室,依然是完全熟悉的马医师。我告诉他们第一次手术太疼了,于是马医师地在我的脸上扎上四针麻药。这一次我能清楚地融入手术室的氛围,有人在拉扯我的脸,但我已经没有痛觉。
我像是一个手术台上的活体实验品,马医师依然边手术便给们讲着:「你们看这个要这样取,很多人都不会。必须全部取出来,所以,每一台手术都要记录当时放了什么、放了多少进去,不能有遗留。」
麻醉还没过,我感觉不到东西流出来,也暂时找不到我的鼻子在哪里。母亲抱住我,泪珠像是夏日的骤雨,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。
哭是因为委屈,但也有内心难以的欢喜:因为手术没有失败,没有毁容,接下来是漫长的伤口恢复护理期--马医师说,取出后不会再反复了。也还因为,即便我自己没有勇气叫停整形,可事故之后,我又获得了重新做我自己的机会,回到出发点,自己开花,自己长大,自己经历,为自己做决定。
我也错了,我习惯性逃避,让自己服从于大多数,地,不彻底,放弃不彻底,快乐也不会彻底,唯有这期间,的感,是彻彻底底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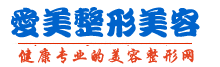



网友评论 ()条 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