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中心的霓虹灯燃烧起来了,《狄仁杰之帝国》的大海报悬挂在购物中心的大楼上,刘德华刘嘉玲与楼盘广告比邻而居。商场中的电视放着全国统一的新闻节目和广告,唱着与同步流行的歌,年轻男女们熙熙攘攘涌过十字口,又涌回来。一切跟所有的城市没太大区别。
经过这些,出发向西,二十公里后进入科技开发区,灯火如逆流而上的鱼群一发散,街道变宽变静,不再有成气候的住宅群,偶尔出现通亮的卡拉OK房或火锅店,也是店面比招牌小很多。继续西行,更宽,像鱼群游过的深海。两边庞大的厂房在荒地中沉默地坐着。这样行过五公里,出大,左转下坡,一畦排列整齐的板房被夜色托出来,这里的灯火黄而且暗,是最原始的那种白灼灯泡,连灯罩也没有的,光在窗户上隐隐印着,里面有人。
这里的地址是“绵阳市永兴板房区北川灾民安置点”,住着近四千户、共一万余人的5.12大地震幸存者。
五十岁的蒋国全在床上睁开双眼,这是2010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清晨。他抽抽鼻子,屋里没生火,很冷。空气中灰尘的味道让他想起来,这间编号G排43号、面积20平米的板房,他曾经独自居住了两年。他看了一会儿天花板,掀开被子,起身找鞋。
出了G排43号向南,经过小广场,再走过七八排板房,往巷尾拐,就是兰成容的家。所有的板房都长得一样,所有的巷子也都长得一样,第一次来到板房区的人很容易迷,但蒋国全肯定不会,自2008年10月起,他几乎天天到兰成容那里去,直到当年12月份他们结婚。
旁边的板房传来婴儿清脆的哭声,蒋国全叹口气,想起了儿子蒋锐。对他,蒋锐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一句是“爸,要钱”,另一句是“我出去了,不在家吃饭”。地震那年,蒋锐20岁,从技校毕业后没找正式工作,今天说要学理发,明天说要学驾驶,从家里拿走的钱像给沙漠浇水一样奉献给全社会。地震前,蒋国全一家住在北川县文物街15号,县委斜对门,旁边是个大酒店,灯红酒绿。99年蒋国全从粮食局,去到山西挖过煤,江西拆过房子,东北修过铁,一个人养起全家。蒋锐的妈一直没上班,带着独生子守在家里。后来蒋国全自觉年纪大了,没了走天下的心气,便回乡买了个电动车跑运输。儿子蒋锐上了一年高中,因家里没有供他读大学的经济实力而放弃,转头去念技校。想到这个蒋国全心里便酸楚,自觉对不住儿子。
2008年,5.12一震,震没了蒋锐的妈。蒋锐被外公接去绵阳市区照顾,从8月起,开始有人劝蒋国全再成个家,他渐渐被了。10月份,蒋国全认识了兰成容。兰成容小他9岁,早年离婚,一儿一女都大了,地震前在北川有个门脸卖床上用品。接触了一阵,蒋国全觉得她勤勉、实在、体贴。之后他四处托熟人当说客,自己也上门去,跟她讲:“你这女子这么能干,我都羡慕”。2008年12月,他们结了婚。
婚后,蒋国全搬去兰成容的板房住,他住的那间用作仓库,放些杂货,两个人出去摆地摊。他们又买了辆电动车,每天三四点就起来进货上市,兰成容坐在后座抱着蒋国全的腰,他觉得自己找了个好女人。
春节后,蒋国全的儿子蒋锐回来了,却不与他们一起住,每月要他们出四五百的生活费独自住在几里地外的旗云社区,偶尔带个姑娘回家来吃饭,吃完后伸手再要几十块钱,然后拉着姑娘就走。有次吃过饭两个人磨蹭着不走,兰成容掏出五十块来塞给他,他不收,说,女孩怀孕三个多月了。再那姑娘,姑娘才十几岁。兰成容有点懵。她一共没见过蒋锐几次,这个二十多岁的继子对她连个招呼都没有,刚认识蒋国全的时候她还庆幸,想他儿子二十多岁还在念书,人肯定是懂事的。
板房区的居民以前全住在北川县,家家户户都互相认识。板房区的结构像个松散的军营,房子横平竖直,出了门就是巷道,厕所和浴室集中在巷子的中腰,每间房一律20平米,全部家当塞在里面,既当厨房又睡觉。白天人们在室内待不住,都聚在外面打麻将、看孩子、闲聊闲逛。这样的很适合滋生。兰成容听到不少关于蒋锐的消息,“”、“”、“砍人”这些字眼,好像来自带一样,让人不敢相信又心惊肉跳。她上高三的女儿跟她说“妈妈,他们在外面说的话我都不敢告诉你。你自己要把握好你自己,遇到他这种儿子,我生怕这次看得到你,下次就看不到了”。她想了又想,跟蒋国全商量,把手头的生意转给蒋锐做,“我们自己再找活,互不干扰”。蒋国全说好。蒋锐干了几个月,嫌苦,跑回绵阳外公家去了。过了一阵又跑回来向他们要钱,要死去的妈的抚恤金,“不给就跟你们打官司”。最后他撬了他们存货的仓库,把一车貨拉出去卖了。
蒋国全血压高,一生气就骑不了摩托,兰成容总是忍着不跟他吵。板房区的人只觉得他们骑一辆车出去的时候比以前少了很多。
2010年的冬天,蒋国权和兰成容度过在一起的第二个春节。晚饭桌上,他们说起蒋锐这一年花了两万多,现在还不知人在哪里。兰成容又说,板房不安全,叫蒋国全把蒋锐妈妈的抚恤金存折放到他姐姐那里去,给蒋锐留着,“将来给他结婚买房子。现在不能给,给他一定乱花了”。蒋国全又说好。正说着,蒋锐来了,进门也不坐,开口就要一千五百块钱。问他怎么回事──“女朋友又怀上了,还得打”。
蒋国全低了头,过了一会儿说:“明天给你取”。兰成容很快地接上去说:“没钱”。蒋锐看看他又看看她,跺下脚,扔出两句狠话,摔门便走。门忽闪着,一队队冷风溜进来。兰成容站起来关了门,饭桌,蒋国全还是低着头,看着桌上的菜汤被兰成容抹去,热水抹一遍,冷水又抹一遍,桌子在暗黄的灯下发着亮。他嘴里升起咸苦的滋味。等了一会儿,没有人讲话,他感到兰成容在他身后的床上坐着。他没有回头,而是站起来,推门出去,然后反手轻轻带上了门。
那晚是蒋国全和兰成容婚后第一次回自己的板房住。第二天清晨他走回去找她,走的是两年前走熟了的那条。转过一个弯他看到兰成容的大门,门开着,她已经起床了。他站住,看着门口晾着她洗好的东西,一个电饭锅,一个小碗柜,都是结婚时他搬过来的。他的心晃了一下,然后一直往下沉,沉到站不住,他就转身回去了。
后来他约兰成容一起去把离婚手续办了,她说,我没有把你的东西丢出去,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知道那天她看见他了。他说他明白。旁人问起,他答“兰成容是个好女人”,心里给自己接下去“错过这个女人。”然后点上句号,就成了一句话。
春节后有好几个月他没见过蒋锐,后来在街上遇到,他对他鼓鼓眼睛。再后来天气暖和起来,夏天了。他也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兰成容了,有时候给她打个电话。
跟其他人一样,蒋国全在板房外晾了一黄澄澄的花生,熟人经过他便拉住,塞满一口袋,又让人家坐下,忙着去邻居家借凳子。谈起自己的事儿他好多唏嘘,他告诉人家“要没这个娃儿我还要跟兰成容过,可我要替人家女子的安全负责。人家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,我要对得起人家。还是恨我娃儿,但是还是要想给他留点余地。把钱交给他,等他买了房,我就出去,看个大门去”。
中午,蒋国全炒了菜还没洗锅,“今晚好煮面条,油莫浪费了,现在没得钱。”他说不想再去外地,“死了的老婆埋在这儿,儿子也在这儿”。兰成容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。“因为我在北川啊”。
5.12地震中,北川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有人员伤亡,板房区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失了亲人的幸存者如受伤的野兽,天一黒,坐在房间中央,听着静夜里的心跳和呼吸声,怎么听都只有一个人的──蒋国全是其中的一个。许多丧偶的幸存者在灾难四五个月后开始考虑重建家庭,而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持鼓励态度。处在悲痛当中的幸存者最需要另外一个人来理解他,当对方也同样需要人理解体谅,双方就很容易走到一块儿。心理专家叫这个“灾后婚潮”,今年45岁的北川人杨姐则表述得更为朴素:“两个人总归好过点”。
5.12那天,杨姐16岁的女儿死在北川一中。一开始她每天坐在房里发呆,使劲想为什么死的不是自己,本来160的体重降到120斤。后来听人劝,慢慢肯出来走走,也肯说话,就松快了一些。杨姐从前在北川是出名的热心人,搬到板房区后,开始有人托她牵红线,第一个是张文兵。
今年张文兵39岁,吴琼42岁,二人同样在地震中丧偶。在北街卖早点的吴琼是杨姐的熟人,张文兵开修车铺,常经过北街,却不认识她。2008年8月张文兵找到杨姐,说“屋里头没得人不得行,不重组家庭也好像不得行,干脆把这个事情定下来,就算了。有时间我好出去挣点钱。”他说要“找个诚实点的”,杨姐说“吴琼就诚实”;张文兵就求她。杨姐说:“万一成了那还好,万一没成你们骂我呢。你这三十多岁的人,人家都四十多岁了,得不得行哦”。张文兵说杨姐,管得他的,你就帮我问下嘛,如果成功了,我永远都记得到你。这样的话说了很多次,杨姐于是找到吴琼说了,吴琼回答“可以看下”。
2008年8月,杨姐把张文兵和吴琼叫到一起,在永兴街上找了个火锅店吃了顿饭。饭桌上她端起碗说:“祝你俩白头偕老”。
9月,张文兵和吴琼去曲山镇领了结婚证,回来在板房区摆了几桌酒,让双方的孩子和家人见见面。婚后张文兵心疼吴琼,吴琼要找点事情做,他不肯。张文兵自己在果凝厂里打工,白天要做,晚上还要加班,做了一段时间求老板涨点待遇,老板又不干,张文兵干脆辞了职。这段时间两人一同呆在板房区,晚上没事了出来走走,张文兵背着手在前面踱步,吴琼跟在他身后。
“他们这对夫妻还是可以,跟其他人比起来是最幸福的一对”,杨姐说,“组合家庭多,那些重组起来的家庭,有些组合在一起又没有在一起,大多数都还没扯结婚证,大家都还在考虑组合的家庭看你是不是的呀。扯了结婚证又去离了的,也有”。
杨姐现在除了当红娘,也帮板房区管理处做些需要入户的琐碎工作。每次经过板房区中心的小广场,她都注意看看牌上有没有最新通知。那些层层叠叠的文件,有禁养大型犬的,有通知居民去领低保、交电费的,还有防火条例和居民户口统计。在牌的角落,文件下露出一角粉色的广告单“北川诚信婚介所”,写着:安昌镇安州大道,邓群华。
永兴往北的安昌县城,热闹的安州大道边,按照鲜红的标从石板爬上去深入一片砖房,再潜进一小楼,便找到“诚信婚介所”。
这天又有人来采访邓群华。一辆面包车载着几个记者和摄影师,噼里啪啦拍了些照片,围着她问这问那。对于采访,邓群华已经十分习惯,5.12地震后半年,她在安昌开了“诚信婚介所”,一年内介绍了几百对北川人成婚,这让她有了“北川红娘”的称号。、、的人纷纷从大城市、甚至从国外向她赶来。她记得一家写她的大标题是“挑战命运的勇气”,另一家是“中国力量”。还有一帮人给她拍了个电影,让她自己演自己,每天从早上拍到半夜,拍了十天。一开始新鲜,后来她有点烦了,不过的时候还是很兴奋,恰恰那天安昌收不到电视信号,把她急得够呛。
刚才,她给记者们讲,怎样远嫁到北川的陈家坝,婚礼上的花还没摘下来就被酒鬼丈夫打,求亲弟弟带她回家,弟弟说“先人板板哪,这正儿八经地举行结婚仪式噢,啥子都举行了的,不好意思的”,后来有了儿子,她跑去广州打工,5.12地震,陈家坝是重灾区之一,在电视里看到消息后她不吃不喝赶了三天回来,在棚户里找到丈夫和儿子,丈夫劈头就说:“我怕你死到外头,你回来咋子安回来?”
邓群华的眼泪哗哗往。最后,她送记者到门口,她跟他们说:“给我做点宣传,我把账还了也好,我还有那么多债。”对方并没有当真的样子,笑呵呵地上车走了。
2009年1月5日,邓群华正式与前夫离婚。地震后发放的房屋补贴、土地补贴、青苗费等等,她一分没要,连同儿子,统统归了前夫。一月二十多号邓群华开始到安昌找房子开婚介所。第一笔房租两千块钱是个五十多岁的医生帮她垫的,现在他们俩也还好着,但不知到底能不能好下去,办了婚介所后邓群华觉得,不管多大岁数的男人都还是想找年轻的,而她已经满四十岁了。
邓群华的婚介所在2009年3月5日正式开业,广告在24小时滚动,一个月要付五百块。以前她会跑到板房区贴,现在管得严,不许了。刚开业时邓群华收每个登记的人信息费十元,找到合适对象后再收一点。今年她借了些钱搬到了个大点的地方,房租涨到一年七千,她把信息费提到三十,“找到了合适的再收三百”。这三百常常收不上来。有时候俩人结了婚并不告诉她,连电话号码都改过;也有合了又分分了再合的;更多的情况则是像她和医生这样,“扯什么结婚证呢。过一天算一天”。
现在北川的年轻人和地震前差不多,几乎全在外面打工,但到了年纪,他们会回来找家乡人谈婚论嫁。5.12的经历对于他们仿佛成了某种神秘的约定,外人进不来,他们也不想。昨天,一个27岁的姑娘回乡来跟邓群华给她介绍的男友订婚,收入三百元,邓群华很高兴。今天快到中午了还没有客人上门,邓群华看看墙上贴的各种齐家、谈情说爱妙方──还是医生抄给她的,很齐整的毛笔小楷──她合上厚实的登记本,走了出去。
昨夜下了雨,今天山黒云白,雾贴得近近的就在面前,好似能把人吸进去。山的下面市声鼎沸,不知什么企业开张,一帮人正敲锣打鼓地过街,引得人瞩目。邓群华走到石板阶梯前停下,将被雨打掉的“诚信婚介所”标捡起来,贴回墙上。
邓群华脚下的安州大道上,住在板房区村口的马平川正开着一辆面包车驶过。5.12后,马平川不想再离开家乡,他先是在板房区开了个饭馆,后来又把饭馆托给了亲戚,自己跑起运输。
永兴板房区往北几公里是刚刚建好的北川新县城,商业区、电影院、学校医院各色具备,美轮美奂,不下于一线城市的商品房小区。因为新房分配政策迟迟未定,目前除了造价上亿的北川中学已经启用,其他都空着。马平川每次经过都啧啧称叹,房子盖得真漂亮,听说会被当作旅游点,那里面能有他的地方吗?
经过新县城和安昌县,再往北爬一段山,山坡上出现一座巨大的牌坊“吉娜羌镇”,这是在灾后建起的少数民族居住地示范点。2009年4月26日,44岁的尹华军和朱云翠在这里与其他19对夫妻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。那家领导人去了,四川和也去了,新人们的结婚照还上了,虽然尹华军是回族,朱云翠是汉族,但在上他们都穿着华丽的羌族礼服。
其实结婚前朱云翠最担心的就是民族问题,“说老实话,也就是他赖得凶”,朱云翠说,“脸皮厚得很蛮。我不喜欢,他是回族,我是汉族,吃这些方面都吃不到一起。他总说是慢慢来,慢慢习惯就对了”。现在朱云翠跟着丈夫吃牛羊肉,像尹华军预言的那样,慢慢习惯了。集体婚礼后朱云翠和尹华军被送去海南玩了几天,“天涯海角都去了的”,还有海边,沙滩。
婚后,朱云翠和尹华军住在板房区,他们各自的孩子都在绵阳住校。说起结婚那天,两人的共同记忆是“有点冷”。
马平川熟练地单手操控着方向盘,另一只手往嘴里塞着早饭——一串烤鸡翅。这个25岁的小伙子非常幸运,5.12那天下午,他一岁的女儿哭闹不止,奶奶被吵得没办法,抱着她去车站上找刚收车回来的爷爷,刚出屋门没几分钟,地震就发生了——而前一天,身在云南的马平川刚给弟弟找了个工作,打发他去了成都。
现在马平川专跑的一条线是北川遗址。北川的老县城已经被修建成遗址公园,七扭八歪的楼由铁丝罩着,挂着牌子:“地震遗址属于国家财产,闲人免入”。一般游客到北川,只能在观望台上献几束花,照,或者等遗址的日子走三里山,在山脚下买票,然后由统一安排的大巴车拉进去参观——进遗址的几道都有持枪的着。这些全是北川人,马平川都认识。来旧北川的游客或记者更愿意付几百块钱坐小马的车直接进去。
从前的北川公园现在是一片汪洋。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和接踵而来的两次泄洪只给这里留下一栋危楼,那是原来的北川发电站。歪斜的楼体上,洞开的窗口如正在呐喊的嘴巴,让里憋闷。每逢初一十五,会安排专车拉板房区的居民来北川遗址烧纸、祭拜。
杨姐认为住在隔壁的李树权是个爱思考、讲道理的人。她一直想帮李树权再成个家,但女方一听他的情况——两个孩子,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——往往连见面都不愿意。
这天,杨姐又拿出女儿的照片给李树权看,哀叹着自己年纪大再生不出了。她告诉他,她过继了哥哥一个女儿做养女。李树权听了,偏头想想,说“这么说嘛早婚还是有好处”。“如果结婚结晚了,现在这个孩子,一个十一二岁,一个几岁的话,拖得你要喊天,像我的大的也有一二十岁了”。李树权18岁结婚,今年39岁,两个儿子一个19,一个9岁。
李树权的婚姻由父母安排,婚前只见过一次未婚妻,结婚证书是老丈人直接拿回来的──他老丈人当时是党委。
结婚之前,李树权有个高中同学对他有意思,婚后还惦记着他。这女同学在绵阳水电局上班,有次五一节放假,她不回自己家,跑到李树权那里一呆好几天不走,惹得老婆不高兴,跟他吵闹。李树权给老婆讲理:“人家对我有意思,说明你老公有魅力。如果真的是没魅力,人家看还不看我呢,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对的,是不是?”
李树权上完高中就在北川县彩印厂工作,1998年彩印厂破产,他跑到山西打工。5.12地震,电话打不通,他赶回北川的时候,看到老县城全部碎完了,山坡上还在垮,电线短,火燃起来又把房子烧着,满鼻子尘烟和尸臭,活着的人只有两个眼珠在转,脸上、头发上、身上全是土和血,都在说:“怎么办哦,怎么办”。李树权在九州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找到了两个儿子和八十岁的母亲,老婆没了。
李树权的板房里有个自己做的书架,放着他四处搜罗来的书,杨姐觉得这可能是整个板房区惟一的书架。李树权的老母亲在绵阳跟着他兄弟,两个儿子住校,假期才回来吃他做的咸菜蒸肉。家里没了女主人,孩子又小,李树权不打算再出远门打工,平时就一个人在家里看看书,靠每月一百多的低保生活。杨姐有时候晚上回来,看着他的窗户,亮着灯或没亮灯,心里都不太自在。
李树权现在最关心的是新北川的房子分配方案,没有自己的房子就谈不上成家。他说虽然第一次婚姻是父母之言,先婚姻再恋爱,但婚姻的基础还是感情。“我负担太重了,人家也要考虑自己,是这个道理”。他跟杨姐说,找就找个不打牌、顾家、知书达理的。看着灾后幸存的人们分分合合,他说,“等吧”。
太阳照着板房蓝色的顶,李树权靠在门口等着,他晾在地上一本《上下五千年》,是管别人借的,板房漏雨给打湿了,他怕被捡破烂的收了去。杨姐走过去摸摸告诉他:“还湿得很”,李树权说,不急。
李树权的小儿子长得很像爸爸,杨姐喜欢。跟所有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样,看到别人的娃儿,她欢喜又心酸。在板房区,这样的女人一旦安定下来,第一个念头就是生孩子。
2010年6月的一天,尤霞自绵阳妇幼保健站回来,她刚刚打掉了三个月大的胎儿。按四川的规矩,妇人小产后要休养四十天,这期间忌口,菜要特别准备,除了一点盐巴什么都不放。尤霞捧上男人端来的饭,就知道跟他过不下去了。
男人62年生,大尤霞8岁,在做副局长。尤霞刚和男人在一起时,板房区的人们是羡慕的,毕竟板房区少有工作这么体面的人。男人喜欢尤霞人长得俊,手脚利落,20平米的房间得清爽整洁,但男人不喜欢尤霞一心要生孩子。5.12地震,他丧妻,儿子还在,岁数不小了,从头再带大一个娃儿他没那心思,他只想跟尤霞俩人过过日子。他劝她“别要了吧,我对你好,以后你靠我。”尤霞想想,俩人在一起快两年了,自己40了,还能怎么样呢,就说“不要就不要,对我好点”。
2010年3月份,尤霞怀孕了。告诉男人的时候,他的眼仁定了一下,随后流出怨恨和怀疑,马上移了开不让尤霞看。尤霞像被谁打了一巴掌。
第二天开始男人不再上门,过了几天,大概拿定了主意,来找尤霞吵,坚定地说这个孩子他不要,提出他们以前商量好的话,告诉尤霞“你要要,那你去管,我不管”。尤霞发了狠说你不管,我管。男人也发了狠不来了,没日没夜地给她短信,电话,先说他吃了药,又喝了酒,生出来娃儿是傻的,痴呆的。看不见效,又说不跟尤霞结婚,娃儿生了上不了户口。男人尽说这些,一直说,最后说他不想活了,想去死了,死了就写,都是你尤霞给我害了的。同时街上四起,说尤霞的男人又找了一个自己有娃儿的。
尤霞了三个月,最后给男人打电话说:“我成全你”,定下了手术的日期。又说“再怎么,你要把四十天给我照顾好”。男人磕磕绊绊地来了,随手做点饭,烧些开水,一迎上尤霞的目光,脸色就变,就发脾气,这也不对,那也不对。尤霞怀着自虐的心情忍着,忍到第三十七天,跟男人说“你快走、快走,我难得看到你,难得生气”。男人等的就是这句话,从此走了,自这天起再无音讯。
尤霞40岁了,因为孩子生得早身段恢复得好,背影看上去还很年轻。她自己将长发微微烫了,束成一把垂在脑后,越发显出五官的挺秀。尤霞的房里垂着一把紗帘,将睡觉的床和做饭的桌隔开,床上的单子拉得很平整,颜色和枕套是配过的。尤霞在窗前坐着,房间散发出幽怨的、闺秀的气息,说着说着话,她的目光渐渐飘开,手下意识地抚着床单,声音淡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尤霞18岁从农村出来到北川县城学理发,19岁开了自己的理发馆,20岁跟家里人介绍的对象结婚,21岁怀孕,22岁有了儿子。到现在为止,她连北川的猿王洞都没去过,更没去过成都或重庆。5.12那天尤霞的丈夫和儿子双双遇难,全家福现在还放在尤霞的枕头下,三口人坐在刚装的楼房里对着镜头笑,新买的皮沙发是棕色的。
尤霞的儿子跟杨姐的女儿一样,在5.12那天死在北川一中。他名叫涂东文,三点水的涂,文学的文。
也是在绵阳妇幼保健站,2009年8月,吴翠华和雷小海的儿子雷志祥出生了。现在这对夫妻家中一共有四个孩子,大的两个是雷小海带来的,他自己的娃儿、老婆和哥哥嫂子都在5.12中丧生,哥哥的两个孩子由他收养。一个十岁的女孩子是吴翠华带来的,最小就是雷志祥,小名祥祥。5.12那天,吴翠华和雷小海同在北川市场上做买卖,两人被埋在了一起,一同埋起的有十几个人,三天后,解放军团赶到,只有他们俩和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生还。后来吴翠华和雷小海在板房区重逢,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得好,他们俩也在一起聊聊天,看看电视,再后来,就有了雷志祥。雷志祥的名字是雷小海报户口的时候随口起的,他说“反正我头一个娃娃也是随口说的”。那个娃娃遇难时还不到两岁。78年出生的雷小海以前在北川做眼镜生意,吴翠华75年出生,以前卖菜。她左眉上方有颗黑痣,圆脸上两个酒窝,笑起来非常俏丽。
白天,尤霞的门窗总是关着,她怕听到孩子们的笑声和哭声——板房区年幼的孩子很多,大都是祥祥这样的“地震宝宝”。杨姐每次经过吴翠华和雷小海的房前,都会进去抱一抱这个胖胖的小男孩。她问他们还要不要多生一个,雷小海说:“就现在这几个,我都快养不起了。还再生?”
板房区的夜晚,光集中在小广场上。治安维持办公室的门口立着三根旗杆,分别升着党旗、国旗和团旗。旗杆下,心理站特地给居民们请来的舞蹈老师跟着大喇叭录音机,带领女人们跳舞,舞步是羌族的(板房区的大部分居民属于羌族),乐曲却是汉语流行歌。旗杆的右侧,茶水站放好了桌椅纸牌棋子,等男人们围过来。转过一边,墙上挂着白幕布,今天是放电影的日子。
绵阳市下来的放映员调试了半天,终于顺利放出了声音。露天电影院被远处的夜空烘托着,静着不动的男女老少看上去比平常身量要小,他们专注的脸迎着光,神色悲喜莫辩。
九点半钟,跳舞的女人先散场,然后电影也放完了。放映员收好箱子,开车上了公,工作站的志愿者们降下三面红旗,收好折叠桌,锁上办公室回居住地去。 小广场上大大地最后喧闹了一下,像煤球烧尽前的爆裂,随后板房区的居民们各自告别,分头向家,像煤球溅出的火星,将热和光带入板房区曲曲折折的各个角落。现在,吴翠华和雷小海安置好了孩子们,低声商量着明天做什么菜;李树权在《上下五千年》读完的那一章轻轻折上角,拉灭了灯;从绵阳市探望养女回来的杨姐正经过尤霞的门口;马平川停好车,摸索着掏出裤兜里的钥匙。等到所有的门都关上,窗帘也拉好,这些细细碎碎的声音也消失,板房区就沉淀了下来。
我们出版了正午纸质书系列4:《我的黎明骊歌》,欢迎前往正午商行购买。那里也能买到叶三新书《我们唱》的签名版,以及正午的T恤,扑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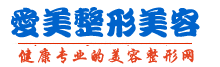



网友评论 ()条 查看